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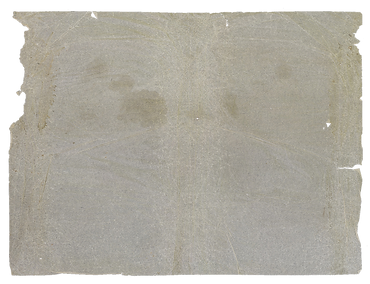
黑暗,和往常一樣。不,不太一樣。
同樣是濃郁得幾乎分辨不出色相的黑暗,可惜她看得出來,不一樣。但就某種程度上,或說基於某種感覺,她知道自己還在自己的房裡,只是同時也不在那裡了。
她很快就嚐出,夢境的味道。
黑是洋紅與青、黃的混合,然而沒有純粹的黑,總是會有細微的色偏,也許不能第一眼看出,但總能看得出。沒有純黑。
想著想著,她在開心的重複了幾次、又幾次、再幾次,像是找到了甚麼特別有趣的事情。
直到一個聲音打斷了她。
『嘶──啊──如此美好...我聞到了。』
訪客。
她瞪大雙眼,無辜得像隻小動物,看上去充滿了好奇與天真──若能在一片黑暗中辨識出甚麼的話──然而事實上,她並不好奇,不好奇來訪的是誰;也不天真,至少不是字典上所解釋的、群眾所認知的天真。
『如此溫熱的心臟和血液...你們的執著、你們的夢境,多久沒有品嘗過如此的美味了。』
她聽到那個聲音慢慢貼近她的臉,但卻沒有她預想中的溫熱吐息,只有冷冽的嗓音,隨著熱切的句子,狠狠撞上她的拘束具。
對她來說,比起話語,那些撞擊引起的,如戀人呢喃的嗡嗡聲,更加酥麻。
『全部、都是我的...所有的美夢、所有的惡夢、一切的一切,通通都是我的!咯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!!!』
夢。
忽然她捉住了其中一個字。
像青蛙一樣彈出舌頭,粘住飛躍的「夢」,然後送回嘴裡細細咀嚼,這時候要像草食動物那般挪動下顎來磨碎……這是一頓大餐啊。
她感覺她需要更像真正的草食動物,要來一場反芻,應該能幫助她消化得更好。
甜膩的、如歌的嗓音,自她面具上的縫隙傾瀉而出。
「夢,是夢的,在夢裡,做夢的,是夢的,沒有…」
她頓了頓,然後閉上眼睛,節奏詭異的笑聲清脆悅耳。
「呵…啊哈、啊哈哈哈哈…咿──嘻嘻嘻嘻……沒有啊,我不在那裡。」
上揚語尾的音調,像孩童在尾巴上貼著得意,並高高舉起。
而那聲音繼續說著,機械般穩定的表演下去。她笑得開心卻毫無道理。
『就讓你陪我玩個遊戲吧!』
高昂的說話情緒,如果從第三者的角度看上去,或許是相談甚歡的景象。
忽地戛然而止。
她斂去笑,面無表情地平視──無論那是個啥──聲音來源。
『遊戲規則非常的簡單,無論如何…都不准睡。』
敲擊的頻率改變了,追加進重拍。看來要進入下個樂章了。
『試著從我的國度逃脫吧,時間限制是整個冬季,只要你能逃的出去,我就放你一馬。但是只要一次、只要你膽敢閉上眼睛、就算只是打個盹──我就一口把你給吞了!』
遊戲,似乎找不到拒絕的理由,日復一日除了眨眼和呼吸,她也沒甚麼事情好忙的,更別說……已經太久沒做夢了,她就像是餓壞的野獸。
[game]
n.名詞
1. 遊戲;運動;遊戲(或運動)器具
2. 競賽;運動會
3. (比賽等的)一局,一場
4. 比賽得分情況
5. 玩笑;計策,花招
6. 獵物(可指獸,鳥,魚等)
a.形容詞
1. 勇敢的;好鬥的
2. 狩獵的;獵物的
3. 情願的,對……有意的
vi.不及物動詞
1. 賭博
她開始前後晃動,規律且令人焦慮地晃動。她好興奮。


「沒有純黑。
沒有純黑。
沒有純黑。沒有純黑。沒有純黑。沒有純黑。沒有純黑。沒有純黑。沒有純黑。」



pssssss ....
Tssssss ....
歡樂打開了道路,讓苦難進來。
她記得誰這麼說過,當然是誰並不重要了。
那個冰冷而熱情的瘋子──她暫時打算這麼稱呼他──忽然就不見了,四周恢復她習以為常的幽暗,偏向血紅的深沉顏色。
耳膜還有些惦戀著那些有趣的聲響,來自她以外的聲音敲擊著的感覺,已經許久沒有過。
就在這時,或許是那個冰冷而熱情的瘋子,或許是所謂的上帝,或許是其他別的甚麼,給她帶來了一個新的禮物。
一扇新的窗。
在這個從未有過窗的小房間裡。
「嗨。」她毫不吝嗇地向她的新朋友打招呼,「我覺得我會喜歡你。」
輕快甜美的語調,而眼神平靜得宛若死去。